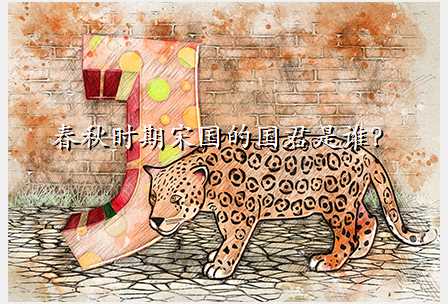
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是谁?
春秋时期,齐国内乱时,宋襄公帮助齐公子复国,代齐作为盟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泓水之战后,宋国国力受创。宋景公时期灭曹国,国力渐盛。战国时期,宋康王“行王政”,实行改革,宋国强盛起来。公元前286年,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齐、楚、魏三国联手灭掉宋国,瓜分宋国领土。 名 家族关系 生卒年 谥号 备注 见 举之子 ?~前800年 宋惠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不详 见之子 ?~前800年 宋哀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撝 宋哀公之子 ?~前766年 宋戴公 葬于河南商丘三陵台 司空 宋戴公之子 ?~前748年 宋武公 葬于河南商丘三陵台 力 司空之子 ?~前729年 宋宣公 葬于河南商丘三陵台 和 力之弟 ?~前720年 宋穆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与夷 力之子 ?~前710年 宋殇公 被杀,葬地待考 冯 和之子 ?~前692年 宋庄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捷 冯之子 ?~前682年 宋闵公 被杀,葬地待考 御说 冯之子 ?~前651年 宋桓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兹父 御说之子 ?~前637年 宋襄公 葬于河南商丘睢县城北 王臣 兹父之子 ?~前620年 宋成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杵臼 王臣之子 ?~前611年 宋昭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鲍 杵臼之弟 ?~前589年 宋文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瑕 鲍之子 ?~前576年 宋共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成 瑕之子 ?~前532年 宋平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佐 成之子 ?~前517年 宋元公 葬于河南商丘旧城区地下待考 头曼 佐之子 ?~前453年 宋景公 葬于河南商丘虞城连中馆
春秋战国之宋国详细历史~!
宋国始祖微子 微子名启(汉代因避景帝刘启之讳,改启为开),殷商贵族,帝乙的长子,殷商最后一个王纣的庶兄,周代宋国的始祖。初封于微地(今山东省梁山西北一带),后世因之称为微子启(或微于开)。殷商末年,纣王无道,穷奢极欲,暴虐嗜杀,导致众叛亲离,国势日衰。微子屡谏,不被采纳,乃惧祸出走。周武王姬发灭商,微子自缚衔壁乞降。周公旦平定管蔡武庚叛乱后,成王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以示不绝殷商之祀,国号为宋,爵位为公,准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 宋襄公霸业的破灭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发生的泓水之战,是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一次作战,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因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之一。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各国诸侯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成为一片散沙。齐国因内乱而中衰,晋、秦也有各自的苦衷,暂时无力过问中原。这样,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就企图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为中原列国目为“蛮夷之邦”的楚国的北进势头,引起中原诸小国的忐忑不安,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可是在当时,宋国的国力远远不逮楚国,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造成宋楚间矛盾的高度激化,楚国对当年的齐桓公是无可奈何的,但这时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结果终于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且说宋襄公专心致志争当盟主,虽然雄心勃勃,但毕竟国力有限,因此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政治号召,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议,轻车简从前往,结果为“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了起来。 楚军押着他乘势攻打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幸亏太宰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匹,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是先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囚俘的面子。大司马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宋襄化的庶兄)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可是宋襄公却振振有词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如果上天不嫌弃我,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执意伐郑。郑文公闻讯宋师大举来攻,立即求救于楚。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事态十分严重,不得已被迫急忙从郑国撤军。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军返抵宋境。这时楚军犹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途中。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屯军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等待楚军的到来。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 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 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悉为楚军所歼灭。只是在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下,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泓水之战就这样以楚胜宋败降下帷幕。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实在糊涂。可是宋襄公本人并不服气,在那里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可见其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因而遭到公子目夷等人的严厉批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他的争当霸主的夙愿,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了。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遗憾的是,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 当然在宋国臣僚中,也不是人人都像宋襄公这般迂腐的。公孙固等人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他们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体现了“兵者,诡道”、“攻其无备”的进步作战思想,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运用。如孙子就把“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定为“处水上之军”的重要原则之一。至于实践中以“半渡击”取胜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 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愚蠢的宋襄公 宋襄公见齐国发生内乱,就通知各国诸侯,请他们共同护送公子昭到齐国去接替君位。但是宋襄公的号召力不大,多数诸侯把宋国的通知搁在一边,只有三个小国带了点人马前来。 宋襄公率领四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国一批大臣一见四国人马打来,就投降了宋国,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 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国,如今齐孝公靠宋国帮助得了君位,宋国的地位就自然提高了。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这次他约会诸侯,只有三个小国听从他的命令,几个中原大国没理他。宋襄公想借重大国去压服小国,就决定去联络楚国。他认为要是楚国能跟他合作的话,那么在楚国势力底下的那些国家自然也都归服他了。 他把这个主张告诉了大臣们,大臣公子目夷不赞成这么办。他认为宋国是个小国,想要当盟主,不会有什么好处。宋襄公哪里肯听他的话,他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开个会,商议会合诸侯订立盟约的事。楚成王、齐孝公都同意,决定那年(公元前639年)七月约各国诸侯在宋国盂(今河南睢县西北,盂音yú)地方开大会。 到了七月,宋襄公驾着车去开大会。公子目夷说:“万一楚君不怀好意,可怎么办?主公还得多带些兵马去。” 宋襄公说:“那不行,我们为了不再打仗才开大会,怎么自己倒带兵马去呢?” 公子目夷怎么也说不服他,只好空着手跟着去。 果然,在开大会的时候,楚成王和宋襄公都想当盟主,争闹起来。楚国的势力大,依附楚国的诸侯多。宋襄公气呼呼地还想争论,只见楚国的一班随从官员立即脱了外衣,露出一身亮堂堂的铠甲,一窝蜂地把宋襄公逮了去。 后来,经过鲁国和齐国的调解,让楚成王做了盟主,才把宋襄公放了回去。 宋襄公回去后,怎么也不服气,特别是邻近的郑国国君也跟楚成王一起反对他,更加使他恼恨。宋襄公为了出这口气,决定先征伐郑国。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可厉害,他不去救郑国,反倒派大将带领大队人马直接去打宋国。宋襄公没提防这一着,连忙赶回来。宋军在泓水(在河南柘城西北,泓音hóng)的南岸,驻扎下来。 两军隔岸对阵以后,楚军开始渡过泓水,进攻宋军。公子目夷瞧见楚人忙着过河,就对宋襄公说:“楚国仗着他们人多兵强,白天渡河,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咱们趁他们还没渡完的时候,迎头打过去,一定能打个胜仗。” 宋襄公说:“不行!咱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敌人渡河还没有结束,咱们就打过去,还算什么仁义呢?” 说着说着,全部楚军已经渡河上岸,正在乱哄哄地排队摆阵势。公子目夷心里着急,又对宋襄公说:“这会儿可不能再等了!趁他们还没摆好阵势,咱们赶快打过去,还能抵挡一阵。要是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宋襄公责备他说:“你太不讲仁义了!人家队伍都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 不多工夫,楚国的兵马已经摆好阵势。一阵战鼓响,楚军像大水冲堤坝那样,哗啦啦地直冲过来。宋国军队哪儿挡得住,纷纷败下阵来。 宋襄公指手划脚,还想抵抗,可是大腿上已经中了一箭。还亏得宋国的将军带着一部分兵马,拼着命保护宋襄公逃跑,总算保住了他的命。 宋襄公逃回国都商丘,宋国人议论纷纷,都埋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更不该那么打法。 公子目夷把大家的议论告诉宋襄公。宋襄公揉着受伤的大腿,说:“依我说,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就别再去伤害他;对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当俘虏。” 公子目夷真的耐不住了,他气愤地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那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 宋襄公受了重伤,过了一年死了。临死时,他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要报这个仇。我看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翼城东南)的公子重耳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是个霸主。 你有困难的时候,找他准没错儿。”
文言文翻译宋王谓相唐鞅曰:“
原文: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 翻译: 宋王对宰相唐鞅说:“我杀过的人非常之多,但是群臣越来越不害怕我,原因是什么呢?”唐鞅回答说:“大王您所降罪的人,都是不好的人。降罪给不好的人,所以好的人就不害怕您。大王要是想让群臣都害怕您,不如不分好坏而杀之,那么这样群臣就害怕了。”没过多久,宋君杀了唐鞅。唐鞅的答复,还不如不答复。 宋王是残暴好杀;乐于采纳意见 老唐是作茧自缚搬石砸脚自作自受 言论是否永远无罪──唐鞅招杀 宋康王问相国唐鞅:“我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但是臣民还是不怕我,这是为什 么?”唐鞅说:“主公杀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只杀有罪的人,没罪的人当然不必 害怕。主公想让臣民害怕,就要不管有罪没罪,时不时地滥杀无辜。那样臣民就会 人人自危,对主公非常害怕了。”康王觉得有理。过了不久,就把唐鞅杀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寓言。虽然我一向对“昏君有过,奸臣有罪” 的论调很不满意,认为奸臣大抵是替暴君背黑锅。但在这篇寓言中,我认为唐鞅确 实比宋康王可恨得多,完全是死有余辜。 可以设想,此前宋康王也曾问过唐鞅:“为什么我对臣民这么宽厚仁慈,他们 却不爱戴我呢?”唐鞅一定是像一千多年后意大利的马基亚维利那样说:“主公, 做君王的不该要臣民爱戴,而该要臣民害怕。你对有罪的人总是重罪轻罚,他们当 然就肆无忌惮啦。只有重其轻罪,主公才会有足够的威严。”于是宋王就开始轻罪 重罚。不料轻罪重罚的效果不佳,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一问。 这里面也隐含着一个悖论。宋康王杀唐鞅,究竟是因为唐鞅无罪还是有罪?唐 鞅一定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宋康王相信了他的话,把他当做无罪的人来开刀。但 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的被杀是因为有罪,并且是不可赦的重罪:教人为恶,尤其是 教唆握有生杀大权的帝王为恶。 所以,我从不简单地认为一切言论都无罪。“言论自由”和“言论无罪”,是 正义者针对暴君动辄对批评暴政的人以言论治罪,而提出的主张。但是从这个寓言 可以看出,正义者未免过于天真。他们以为真理可以越辩越明,真理终将战胜谬论,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只要真正的言论自由实现了,那么邪恶的言论必定不能战胜正 义的言论。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正义的言论,在逻辑层面上固然更为雄辩,但问 题在于,一切邪恶的言论决不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上与正义者进行智慧的较量。所 有邪恶的思想家都是为世俗权力辩护的,所以邪恶的言论必然会借助世俗权力的暴 力,以救济其逻辑力量的先天不足。在历史的正义法庭面前,单独的邪恶言论和单 独的世俗权力固然都无法凭其自身的力量战胜真理;然而在现实的实际较量中,邪 恶言论一旦与世俗权力勾结(而两者必然要勾结),力量对比就发生了逆转,真理 在每一个相对的短时段内就往往落败。而正义者由于坚信真理是自足的,必然不会 借助世俗权力──另外,正义的力量一旦与世俗权力结合,就会迅速变质为非正义 的力量。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壮之处:正义永远在野,而邪恶永远在朝。在每一个短时 段内,邪恶总是胜利。从每一个短时段来看,邪恶战胜正义就是历史的基本主题, 这也正是世俗权力永远相信暴力的原因。在每一个短时段内,暴君及其帮凶总是自 鸣得意地认为正义的力量不堪一击──而从表象上看确实如此。观察能力仅及于历 史短期表象的大部分人民,也同样认为正义的力量不堪一击,所以他们明哲保身地 不向正义者伸出援助之手,而是冷漠而麻木地听任正义的力量被邪恶的势力扑灭。 人民渴望正义,然而他们悲观地认为正义无法在人间实现,所以他们惟有寄望于虚 幻的天国和来世。 但我决不这样看。我认为每个时代的正义力量固然相对地弱于邪恶势力,但由 于同一时代的邪恶势力内部,永远在互相利用而不可能真正联合(康王杀唐鞅即是 一例),因此邪恶势力与邪恶势力之间在精神上的对立,甚至超过他们与正义者之 间的精神对立。也就是说,邪恶在精神上完全是虚弱和孤立的,邪恶与邪恶之间是 永远无法勾通的,因此历史上的邪恶势力不可能给现存的邪恶势力以任何精神上的 援助,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各自占据了一个个邪恶的孤岛。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正义真正地有别于邪恶,真理本质上有别于谬误──正义的力量是包围这些邪恶孤 岛的历史洪流,至少是潜流。不同时代的正义者,在精神上是高度相通的;每一代 被当时的邪恶势力扑杀的正义者,都成为后继者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和力量源泉。 正义者哪怕在每一个短时段内都惨遭邪恶势力的扑灭,但历史上的正义捐躯者永远 在精神上激励后继者。每一个暂时得势的邪恶者,不仅在精神上是孤独的,而且在 历史上是孤立的──连后世的邪恶者也在假惺惺地谴责他们,这更足以证明,正义 在长时段内是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而每一个暂时失败的正义者,不仅在精神上不 是孤独的,而且在历史上更属于一个无形的巨大精神阵营──他们是无须联合的高 度联合体。因此从长时段来看,正义总是会逐渐获胜的。虽然每一个时代的恶势力 往往压倒正义的力量,每一个时代总是比前一个时代更进步。恶势力每一次恶贯满 盈的崩溃,总是为正义积蓄了新的能量。虽然历史并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总体来看, 历史确实在进步,文明确实在发展,正义确实在日益成为历史的主角──否则我就 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在这里严厉批判暴君及其帮凶。 我在本篇中要说的是,言论并非永远无罪,像唐鞅和韩非的言论就有大罪。正 义者既要主张言论自由和言论无罪,但又不能因为主张言论无罪而姑息任何邪恶的 言论。因为所谓言论无罪,是针对禁止人民自由言论的统治者而言,统治者无权禁 止人民的自由言论,统治者无权用国家机器关押和捕杀任何言论者,包括无权诛杀 邪恶的言论者。所谓邪恶的言论有罪,是指那些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混淆视听颠倒 是非的谬论有罪。但是指控邪恶的言论有罪,并非主张用世俗权力对邪恶的言论者 予以诛杀,而是在真理的自由论坛上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哪怕世俗权力以正义自 许,也无权对邪恶的言论者予以诛杀──事实上,又有哪个世俗权力不以正义自许 呢?一旦世俗权力有权审判言论,那么由谁、又如何来判断到底是正义的权力在诛 杀邪恶的言论,还是邪恶的权力在诛杀正义的言论?没有人!也无法判断!而且可 以肯定地说,一旦权力在诛杀言论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邪恶的权力在诛杀正 义的言论,极少例外。即便偶有例外,比如说宋康王诛杀了唐鞅,正义者也不寄侥 幸于这样的例外。更何况唐鞅虽然该死,但宋康王并非由于他的言论对人民有罪才 杀死他的,而是因为他的言论对帝王有功才杀死他的。当然,宋康王一定会以“反 对人民”的罪名来宣布他杀死唐鞅的理由。世上的一切宋康王,在诛杀言论者的时 候,必然会隐瞒其真实意图,而乔扮成正义者的面目。轻信的愚民,于是误以为世 俗权力有权介入真理的论坛,误以为这会有助于真理战胜谬论。我认为,真理根本 无须任何世俗权力的援助,只要世俗权力不介入真理与谬论的较量,真理必然能够 战胜一切谬论,尤其是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绝对如此。
